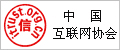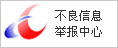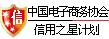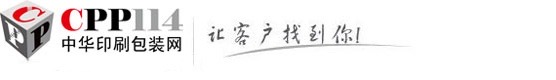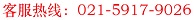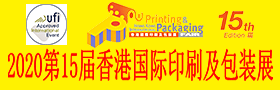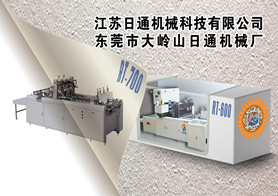荣宝斋木版水印传人张延洲:传承传统工艺
2009-02-04 00:00:00.0 来源:《中国青年报》 责编:石渺薇
北京琉璃厂,有个300多年历史的老店“荣宝斋”,店内展示着一幅绢制的木版水印巨作——北宋画家张择瑞的《清明上河图》,这幅与原作相同的长卷民俗风情画,令人叹为观止,售价高达30万元。
“嗬,那《清明上河图》有5米多长呢,光人物就有1643个,当年我和俩师傅一块儿雕刻,5年才刻完。”年过半百的崇德福对往事记忆犹新,“我们仨刻了1千多块版材,光我就刻了500多块,一块版最长得刻10天。”
木版水印技艺是荣宝斋的“绝活儿”,始自清光绪年间,沿用中国独有的雕版印刷技艺,逼真复制各类中国字画,所用纸、墨、色等原料均与原作相同,其成品“几可乱真”。
上个世纪50年代,荣宝斋的经理把著名画家齐白石请到店中,在他面前挂出两幅《墨虾》,告诉他其中只有一幅是他的真迹。老人端详了许久,最终摇着头说:“这个……我真看不出来。”
2006年,荣宝斋的木版水印技艺,被遴选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崇福德是荣宝斋木版水印技艺的第六代传人。
崇德福的师傅张延洲,是木版水印技艺的刻版高手,他用了8年时间,雕刻出五代南唐画家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46个神态各异的人物,无不精确至极,公认为木版水印的巅峰之作,被故宫博物院定为“次真品”。
张延洲虽然有高超的雕刻手艺,可生性寡言。那时教徒弟手艺靠口传心授,但张师傅就像茶壶里煮饺子——有嘴倒(道)不出来,只让徒弟“多看”,却不具体说明该如何使刀,用多大劲儿,刻什么角度。全凭崇福德自己去悟。
刻版师傅既要懂雕刻,还要有绘画的基础、美学和诗的修养。好在崇福德打小就帮在宫灯厂画画的父亲,勾点儿简单的画,也能画上两笔。业余时间又喜欢逛故宫、美术馆,研究不同画家的风格、用笔的路子,所以能领悟书画的精髓。为了掌握走刀力度,他甚至临摹原作,体会画家下笔的劲头儿。
“哎哟,刻那俩人,可真难坏我了。”他念念不忘刻第一个作品——敦煌壁画“双飞天”时的难度。师傅要求“丝绸衣服的褶皱、飘带的下垂感和头发丝的光泽,都要精确地刻出来。”他废寝忘食3天才刻了一块版,“最难的是飞天的眼神,刻刀偏离一毫米,整个作品就‘砸’了。”
因勤学苦练,出师时崇福德的手艺已达到三四级工的水平,能操刀如笔,灵活掌握走刀力度,将线条的转折、顿挫雕刻出来。
“只要拿起刀,就盯死了,一点儿不能走神。”崇福德说,“尤其是刻人物的脸,五官得一气呵成刻完。一歇刀好像气力就灌不进去了。”
从17岁初中毕业被分配到荣宝斋学刻版,崇福德至今已刻了漫长的36年。虽因长年低头干活,落下了眼花、耳鸣,颈椎骨质增生的毛病,但他敢口出狂言:“拿什么书画来,没有我刻不了的东西。”即使是最难刻的写意画,画家用枯笔干蹭的,如刘继卣画的钟馗,胡须跟一团乱麻似的,他也能刻得一丝不苟。
崇福德的确挺“牛”。从上世纪80年代后,荣宝斋复制的木版水印书画,无论是徐悲鸿的马、鹰,齐白石的虾、蟹,吴冠中的双燕,还是《孙子兵法百家书》……“每幅书画中难刻的部分,都由我来完成。”
戴着老花镜的崇福德,左手拿放大镜,右手持月牙形刻刀,聚精会神地在梨木板上,精雕细刻著名画家黄永玉的《阿诗玛》组画。这本《黄永玉版画》,将参加世界书展。“人家提出得让木版水印技艺的传承人刻,这活儿就交给我了。”崇福德乐呵呵地说。
“坐这儿刻了37年木头,我真有种修行的感觉,好像入到里面去了。”崇福德笑着调侃道,“有了烦心事,只要拿起刻刀一干活就全忘了,说明我已修成正果了。”
眼下,崇福德最担心后继无人,怕这门老手艺失传。他原来有俩徒弟,学了10年,能刻了,走啦。“人家有路子,挣钱多,阻止不了。”他感叹道,“唉,现在选学手艺人很难,有人学多少年不见得能学出来。”现在他有5个徒弟,他推荐大徒弟当头儿,鼓励他们好好干。
当年一起进荣宝斋20多个学徒,如今搞木版水印雕刻的,就剩他一人了。提及此事,他一脸凝重,“我不能走,我走了,这门手艺没有传承下去,我会有犯罪感的。”
“嗬,那《清明上河图》有5米多长呢,光人物就有1643个,当年我和俩师傅一块儿雕刻,5年才刻完。”年过半百的崇德福对往事记忆犹新,“我们仨刻了1千多块版材,光我就刻了500多块,一块版最长得刻10天。”
木版水印技艺是荣宝斋的“绝活儿”,始自清光绪年间,沿用中国独有的雕版印刷技艺,逼真复制各类中国字画,所用纸、墨、色等原料均与原作相同,其成品“几可乱真”。
上个世纪50年代,荣宝斋的经理把著名画家齐白石请到店中,在他面前挂出两幅《墨虾》,告诉他其中只有一幅是他的真迹。老人端详了许久,最终摇着头说:“这个……我真看不出来。”
2006年,荣宝斋的木版水印技艺,被遴选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崇福德是荣宝斋木版水印技艺的第六代传人。
崇德福的师傅张延洲,是木版水印技艺的刻版高手,他用了8年时间,雕刻出五代南唐画家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46个神态各异的人物,无不精确至极,公认为木版水印的巅峰之作,被故宫博物院定为“次真品”。
张延洲虽然有高超的雕刻手艺,可生性寡言。那时教徒弟手艺靠口传心授,但张师傅就像茶壶里煮饺子——有嘴倒(道)不出来,只让徒弟“多看”,却不具体说明该如何使刀,用多大劲儿,刻什么角度。全凭崇福德自己去悟。
刻版师傅既要懂雕刻,还要有绘画的基础、美学和诗的修养。好在崇福德打小就帮在宫灯厂画画的父亲,勾点儿简单的画,也能画上两笔。业余时间又喜欢逛故宫、美术馆,研究不同画家的风格、用笔的路子,所以能领悟书画的精髓。为了掌握走刀力度,他甚至临摹原作,体会画家下笔的劲头儿。
“哎哟,刻那俩人,可真难坏我了。”他念念不忘刻第一个作品——敦煌壁画“双飞天”时的难度。师傅要求“丝绸衣服的褶皱、飘带的下垂感和头发丝的光泽,都要精确地刻出来。”他废寝忘食3天才刻了一块版,“最难的是飞天的眼神,刻刀偏离一毫米,整个作品就‘砸’了。”
因勤学苦练,出师时崇福德的手艺已达到三四级工的水平,能操刀如笔,灵活掌握走刀力度,将线条的转折、顿挫雕刻出来。
“只要拿起刀,就盯死了,一点儿不能走神。”崇福德说,“尤其是刻人物的脸,五官得一气呵成刻完。一歇刀好像气力就灌不进去了。”
从17岁初中毕业被分配到荣宝斋学刻版,崇福德至今已刻了漫长的36年。虽因长年低头干活,落下了眼花、耳鸣,颈椎骨质增生的毛病,但他敢口出狂言:“拿什么书画来,没有我刻不了的东西。”即使是最难刻的写意画,画家用枯笔干蹭的,如刘继卣画的钟馗,胡须跟一团乱麻似的,他也能刻得一丝不苟。
崇福德的确挺“牛”。从上世纪80年代后,荣宝斋复制的木版水印书画,无论是徐悲鸿的马、鹰,齐白石的虾、蟹,吴冠中的双燕,还是《孙子兵法百家书》……“每幅书画中难刻的部分,都由我来完成。”
戴着老花镜的崇福德,左手拿放大镜,右手持月牙形刻刀,聚精会神地在梨木板上,精雕细刻著名画家黄永玉的《阿诗玛》组画。这本《黄永玉版画》,将参加世界书展。“人家提出得让木版水印技艺的传承人刻,这活儿就交给我了。”崇福德乐呵呵地说。
“坐这儿刻了37年木头,我真有种修行的感觉,好像入到里面去了。”崇福德笑着调侃道,“有了烦心事,只要拿起刻刀一干活就全忘了,说明我已修成正果了。”
眼下,崇福德最担心后继无人,怕这门老手艺失传。他原来有俩徒弟,学了10年,能刻了,走啦。“人家有路子,挣钱多,阻止不了。”他感叹道,“唉,现在选学手艺人很难,有人学多少年不见得能学出来。”现在他有5个徒弟,他推荐大徒弟当头儿,鼓励他们好好干。
当年一起进荣宝斋20多个学徒,如今搞木版水印雕刻的,就剩他一人了。提及此事,他一脸凝重,“我不能走,我走了,这门手艺没有传承下去,我会有犯罪感的。”
- 关于我们|联系方式|诚聘英才|帮助中心|意见反馈|版权声明|媒体秀|渠道代理
- 沪ICP备18018458号-3法律支持:上海市富兰德林律师事务所
- Copyright © 2019上海印搜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电话:188166220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