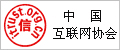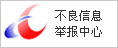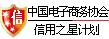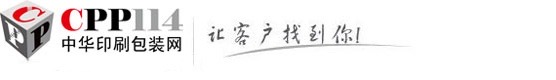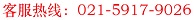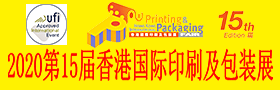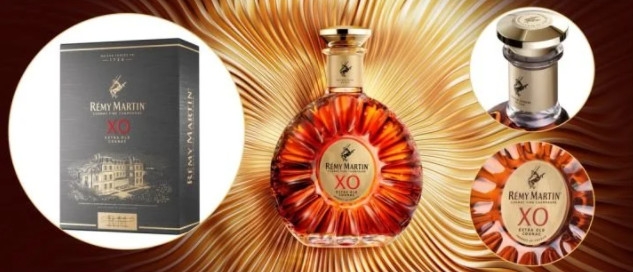大学出版在改革中失却先机:发展遭遇政策瓶颈
2009-12-08 11:03:46.0 来源:必胜网 责编:乐轩
- 摘要:
- 然而,遗憾的是,目前社会、行业对出版业的评价,主要指标就是规模、体量,真正埋头做书的出版社很容易被忽略了。“总署提出‘做大做强’的目标,打造双百亿集团,我们是非常赞同的。但是,我们将来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到底是以什么为主体?现在,各地方出版集团的多元化经营是必要的,但是到什么程度?多元化经营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认为,既然叫出版业,就应该以出版为主业,多元化的目的也是为了推动或促进主业的发展,而不是冲淡主业。”张其友的话或许代表了诸多有着出版情怀的大学出版人的心声。
扩张之途
“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大学出版社还没有一家能够提出切实可行的、或者整个技术路线十分明确的扩张道路,这是让人很痛心的。”贺耀敏表示。
但在陆银道看来,这其中有着非常复杂的原因。其一,是没有政策的扶持;其二,社长们都有想法,但是不敢提,因为大学社社长的任命权在学校,说话也好,做事也好,没谱的事,是不会先讲出来的;其三,对于很多大学而言,仍旧没有将大学社社长看作是职业出版人,走的是一般干部的任命,社长干两届就要被换掉,没有深水不能养大鱼,很多扩张的目标也不及实现。值得指出的是,如果高校的相关主管领导对职业出版人保持一定的敬意,不会出现将其随意调离岗位的情况,出版社往往就能更好的发展,譬如外研社、华东师大社、广西师大社、复旦社、北医社等,皆属此例。
实际上,有综合实力的大学社都在暗中进行扩张之途,北京有五家大学社都在与外地大学社商谈,看有没有合作的可能性。其扩张的路径大致以股份制为主,如果股份制走不通,就互相参股,“先往前拱”。但据本报了解,实质性谈下来的还没有一家。
“现在最大的阻力就是,出版社与出版社之间的整合,比如,大学社与大学社之间的整合,或者大学社重组其他出版社,比如,这次148家中直出版社改制,有的规模很小,我们也曾考虑重组的问题,并且有些出版社也向我们表示了希望重组的意向,但上边没有明确说法,操作起来有困难。”张其友表示。
在陆银道看来,目前阶段,大学社最有可能的合并形式是“托管”。“托管”,即隶属关系不变,牌子不改,只是经营权归另一方,托管两三年,如果合适,就参股,形成“联邦式合作”。但到目前为止,“托管”的形式也未能成行。
但是,外延式扩张也不是不可能,但受限于特定方面,比如,兼并一个图书公司或者发行公司,或者印刷厂,还是有可能的。譬如,北师大出版集团通过股份制改造和技术性改造,将下属的京师印务公司与民营印刷厂进行整合,组建成新的控股股份制印务公司,极大地提高了经营管理能力,完善了生产功能,拓展了产品品种,增强了市场竞争力,实现了优势互补和双赢的效果;同时,北师大社正在考虑以资本为纽带,吸引外部市场营销的优势力量,成立助学读物有限责任公司,外研社最近也会有所动作。
尽管大多数大学社选择的是内涵发展之途,但内涵式发展在一定条件下,也可变为对外扩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贝贝特模式”,走的就是典型的“内涵加外延”模式。譬如,该社总编助理携一些骨干编辑到上海设立办事处,一旦图书规模上来,销售渠道稳定,就及时裂变为上海贝贝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同时,更多的大学社在探讨可行的合作、联合的方式。“比如,在某个业务领域共同投资,组建经营实体,进行资本经营;或者联合投资,明确分工,共同运作较大型出版项目等。”张其友称。在王明舟看来,在数字出版的合作出版方面,大学社的合作有一定的可能性。
贺圣遂则呼吁,既然大学社是以学术出版为特征的,那么,在渠道方面,可以有更多的信息交换,更大的工作平台。“大学社往往有自己的销售渠道,相当一部分学术著作是依靠分布在高校区域的书店来实现销售的,这个平台如果建立得更合理,内部有更多的组织关系来协调,对学术著作的流通会起到更大的作用。”
品牌对抗“航母”
尽管地方出版集团林立,但在陆银道看来,除去市场割据的威胁,集团也并不可怕。“集团组成的个体还是出版社,这些出版个体对大学社来说,并不可怕。事实上,从图书产品的比拼来看,大学社在某些方面更有优势。”
这也是北医社选择内涵发展模式的原因。“无论从发展思路,还是从产品的整体设计,我们都是有理念的。我们喜欢做很好的长线产品,前期运作两三年,做成一本好书,但地方没有这个耐心,产品的研发能力也不如我们这么严谨。只要我们有核心竞争力的长线产品,就不惧市场竞争。”在陆银道对北医社的规划中,北医社只出一流教材,一流专著,以及国际合作共同出版的顶尖医学书。他告诉读书报,某地方精神病医院院长的一本著作,根本无法通过北医的审稿,但拿到地方,毫不犹豫就出版了。“我想办这样的出版社,在业界非常有影响,医学界认为,到我们出版社来出版一本书,是他的荣耀。而产品好,自然会挣到钱。”
对于大学出版而言,大规模的重组联合扩张显然不是发展的惟一之途。譬如,已经在人文社科领域做出品牌的复旦大学社依然会延续其品牌化、特色化道路,出版一流教材和专著,以及高品质的人文社科图书。没有刻意扩张的复旦社从2001年开始,每年发展规模的递增速度都超过了10%,去年达到了3个亿码洋的规模。“但我知道有些出版集团的主业在下滑,尽管体量大,但规模优势在主业上并没有展现出来。所以,我们并不担心在出版主业上与集团的冲撞,关键还是在于出版社的图书质量、特色与品牌。”贺圣遂表示,复旦社将坚持内涵式的发展模式。
同时,贺圣遂也看到了国家已经做出的很多有利于大学社发展的政策,譬如,启动出版输出工程、国家资助项目,“这是一种出版政策,是对建立在以发展文化为基础之上的出版业的真正的支持”。在贺圣遂看来,任何一个中国都有主体出版,这种出版是为这个国家文化主流意识创建、积累和传播做贡献的,但也往往是被完全商业化的出版社忽略的。而文化,“不应该仅仅靠一部分人去做艰苦的支持,而是要靠国家政策调剂的”。
显然,扩张并不是万能的,也不一定“大”就是赢家。“我的担心是,有些地方出版,会不会作废主业?出版有出版的规律,不是说钱越多,投进去,就越能见效益的。出版需要一个总体的积累,有底蕴在里边。给我一个亿,两个亿,我也不可能快速做大,因为我不会做短平快的产品。出版社要长期发展、稳定发展,必须要产品研发的过程。很多大学社,项目从调研开始,找作者,到出版,是以年为周期的,但是现在很多出版社,从网上搜东西,三五天出一本书,这是很可悲的。”陆银道说。
然而,遗憾的是,目前社会、行业对出版业的评价,主要指标就是规模、体量,真正埋头做书的出版社很容易被忽略了。“总署提出‘做大做强’的目标,打造双百亿集团,我们是非常赞同的。但是,我们将来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到底是以什么为主体?现在,各地方出版集团的多元化经营是必要的,但是到什么程度?多元化经营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认为,既然叫出版业,就应该以出版为主业,多元化的目的也是为了推动或促进主业的发展,而不是冲淡主业。”张其友的话或许代表了诸多有着出版情怀的大学出版人的心声。
“我只希望,大学出版人不要成为‘没落的贵族’。”贺耀敏说。
【点击查看更多精彩内容】
相关新闻:
数字出版 出版社的最后一次机会
中国出版集团牵手时代出版 为IPO铺路
春华秋实摄影作品集出版 为新中国60华诞献礼
- 关于我们|联系方式|诚聘英才|帮助中心|意见反馈|版权声明|媒体秀|渠道代理
- 沪ICP备18018458号-3法律支持:上海市富兰德林律师事务所
- Copyright © 2019上海印搜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电话:188166220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