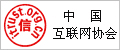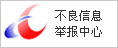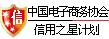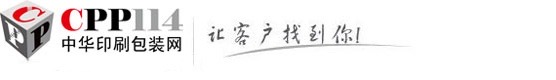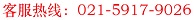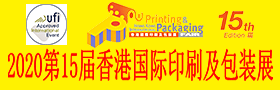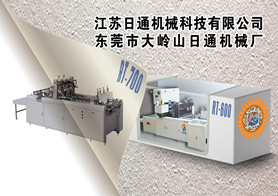出版市场与非畅销书现状分析
2010-03-16 09:40:45.0 来源:北京语言大学中文系 路文彬 责编:涂运
【CPP114】讯:口消费主义原则主导的图书市场无时无刻不在纵容着读者的自恋意识,让读者以为他就是这一方天地里的中心。
口消费指涉的是欲望,欲望是一个空间性概念,而消费本身则也只在当下方存意义。故此,作为时间性的历史和未来皆必然要被逐出消费艾化的地界。
今天,我们每家出版社的选题报告单上差不多都会有"出版方式"这样一栏,上面标明"公费"、"自费"以及"资助"的字样。一项出版选题是否能够被顺利通过,首先取决的不再是作品本身的品质,而是此种品质究竟具有怎样的市场号召力。至于作品将会产生怎样的社会影响,似乎不是出版者首先要考虑的事情。他们真正担心的是自己的投入最终能有多大比例的产出。同其他所有公私企业一样,成本和利润似乎也成了出版社生死存亡的要件。我之所以使用"似乎"一词,是因为出版社的处境和其他企业相比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即使它们正在步入"改制"的进程,却也并未就像其他公私企业那样被迫在市场的火山口上跳舞。今天,企业倒闭已是司空见惯的事实。但我们还从来没有听说中国出版社的倒闭。虽然国家相关法规已有向民间出版机构松动的迹象,但出版社的组建仍旧属于国家行为,中国出版社的特权身份依然没有被动摇。在这个前提下,它们已经开始将自己纳入与所有市场实体平起平坐的地位,着手鼎力打造全盘商业化的运作模式。
国家经济体制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急剧转型,固然使诸多人士和行业产生了明显的不适反应,但也有不少人士和行业做到了从容应对。如果说作者属于前者,那么出版方就该属于后者。于是,学术著作于商业文化时代必然遭遇的命运自然就显现出来了,此种状况在资本主义国家早已不算是什么新鲜经验。问题在中国之所以显得格外醒目,一方面是由于它的头一遭出现,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这些作者们的出版权利(public right)未能得到出版社出版权力(public power)的起码保护。我们当然不会苛责资本主义国家的出版商应该对此类作者提供保护,因为出版在它们那里已绝对是彻头彻尾的商业化行为,出版商的出版权力始终需要听命于市场的指挥棒。而在我们这里,出版社的权力至少在此时还是完全能够独立于商业号令的。可是,出于向市场经济体制表达认同的迫切需要,他们单方面就提前终结了同作者之间的历史默契。多年来,和我们的很多期刊一样,出版社也一直自觉担当着培养作者的神圣使命;有不少作家或学者就是从某一个出版社成长起来的,编辑们是良师,也是益友。但到了这一时刻,他们摇身一变,迅速将自己装扮成了商人。于是,编辑的含义就此发生了质的变革。衡量一个编辑的素质,不再是要看他知识修养的多与少,重点是要看他商业眼光的高与低。作者把书变成了铅字,获得了合法书号,他的可怜目的便算实现了。
上述所指还是中国出版社在商业文化尚未全面渗透整体社会时的一种现状,而随着市场因素无孔不入的染指,以及全球视觉文化一致性的绝对兴盛,中国出版社方才真正开始遭逢些许来自市场的压力。那么可以想象,对于它们来说,除了无所保留地拥抱市场,还可能坚持什么吗?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商业文化繁荣的速度,总是紧随着视觉文化的发展脚步的。从电视时代到网络时代,不变的是人类视觉欲望因此获得的一次又一次空前满足。视觉那喜新厌旧的本性理所当然地将文化的进步理解成了不断升级的消费,事实亦的确如此,没有消费也便没有商业。但是,当阅读本身也变成了一种消费行为时,情况又会怎样呢?
千万别被消费剌激生产从而带来的商业繁荣假象所惑,归根结底,消费就是消耗;其生产过程正是又一次不折不扣的消耗过程,与创造行为所具有的丰富动力实质完全南辍北辙。在每一次带有消费性质的行为当中,我们势必享受的太多,承担的太少;索取的过多,给予得过少。所以,我们发现,摆在面前的图书在装帧、印刷、排版、纸张等方面变得愈发精美,而在内容上却越来越趋于低俗化了。这就是消费性阅读的实情,图像挤压着文字,趣味占领着思想。在消费文化统领一切的时代,唯有这样的读物才可能会有畅销的实力。这没什么好奇怪的,不要忘记,青少年的阅读障碍应是在电视普及之后才呈现出的一个广泛社会现象。电视影像不单消弭着他们的专注能力,也阻碍着他们之于文字的亲近;而网络的出现则促使这一境况更加地恶化了。如此残缺的阅读能力又如何胜任得了既往那些需要动用一定抽象思维的严肃读物呢?于是,因为没有市场,就连过去那些广受欢迎的文学作品也遭遇了寒冬。
不过,大众阅读能力的退化还算不上出版社遇到的最严峻挑战,真正令其痛苦的是读者数量的急剧萎缩。过去,一部普通的长篇小说动辄即可有上百万的印量,而今,印量能够过万就可算作是畅销书了。此外,尽管在人口数量上中国居世界之首,可一旦按照比例换算下来,我们的读者却少得令人汗颜。即便在这有限的读者群当中,受"书非借不能读也"这一传统借口的影响,又有几人愿意负担购书的支出呢?必须指出,这绝非属于个人经济承受能力的问题,而只不过就是消费习惯的问题罢了。我也仅在这一点上能对中国出版社的现有处境抱以同情,确实,同许多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读者不仅是量的问题,质的问题也同样令人悲观。
比较一下便知道了:由于禁不住出版商的怂恿,莱文斯基将自己和克林顿总统在白宫上演的那场丑闻匆匆成书上市,看好了要共同狂赚一把;然而大大出乎其意料的是,该书居然遭遇了美国民众不约而同的坚决抵制,从而使他们的商业美梦在瞬间即被断送。这就是发生在美国的出版事实,它在一定程度上昭示了美国读者的素质。可以设想,假如此书当时得以在中国上市,它有可能也会遭致这样的冷遇吗?可是,在指责我们的读者的同时,我们仍然不能忽略我们的出版社所应承负的社会责任。毕竟,身处印刷时代广大读者的阅读口味是由出版社来塑造的。它们的倾向不仅仅影响着作者,也影响着读者。倘若出版社完全摒弃了培养读者群体的主动意识,那么它们便只能被后者牵着鼻子走,走到最后极有可能就是落得个被抛弃的结局。众所周知,我们的出版社先是紧跟着影视走,后来又是紧跟着网络走,事实证明,它们已经在消费时代读者任性步调的引领下不知不觉跟丢了自己。
过分看重畅销,我们的出版社正在经营的无疑是一项与自我社会地位不甚相称的活计,身份意识已被其自觉置之脑后。资本化运作方式决定了它们所要面对的压根不是什么读者,而是千人一面的消费者。把读者变成消费者,即把读者奉为了上帝。在这种意识的支配之下,出版社的教化功能可以说已经全然丧失,社会精神文明的宏伟事业也因此变得岌岌可危。消费主义原则主导的图书市场无时无刻不在纵容着读者的自恋意识,让读者以为他就是这一方天地里的中心;每一本书都是为他一个人量身定制,每一行字皆是为了让他备感快乐才有了存在的价值。因此,在每一本书的面前,他都不可能萌生丝毫谦逊的心态。对他而言,一本书就是一件小小的商品,它的到来只是以为他的生活提供日常便利为宗旨,其中并无什么神圣可寻。商品从不指导我们的生活,它仅仅听命于我们作为主人的指使。顺乎这样的情境,书籍固有的一切内涵差异统统被遮蔽了。精英/大众、高雅/通俗、严肃/调侃等既有鸿沟被一一填平,这看似民主平等的胜利表象蕴涵的不过就是商业的霸权实质,正如后现代主义表面上之于一切权威的反叛,所欲表达的不过就是针对消费权威的顺从;其指归说到底乃是对于历史的无情取缔。
今天,我们许多人极为反感对所谓纯文学的认同,其内心实际上就是在表达着对于历史的急切拒绝以及对于当下俗文学现状的无比满足。消费指涉的是欲望,欲望是一个空间性概念,而消费本身则也只在当下方有意义。故此,作为时间性的历史和未来皆必然要被逐出消费文化的地界。一件精美的商品既没有历史,也不需要未来,它属于且只属于当下。消费实践的空间动力学仇视一切可能生成历史价值的商品,当然那些只为收藏而存在的商品除外(有必要说明的是,在此收藏行为本身同样亦暗含着一个消费的过程,故而使得其对象与其他商品的消费本质并无冲突)。正是基于如此一种念头,权威的
《人民文学》杂志在去年终于放下纯文学的架子,向阵营之外的郭敬明伸出了橄榄枝。并不是编辑们意欲否认阵营界限的存在,而是郭敬明加入所带来的期刊销量激增,让他们暂时可以忘却这一界限的存在。把期刊视为商品,纯文学相对于俗文学的优势亦便自动失效了。
似乎没有什么好责怪的,既然消费主义话语不给历史以任何的发言权,那么我们的出版机构也就有理由不选择坚持了。非畅销读物只要没有来自权威层面的压力,它们便干脆一概将其挡在门外。但为此受到损害的不仅是非畅销读物作者的出版权利,还有非畅销读物读者的阅读权利。可是又不能不承认,这数量极其有限的一部分往往就跟我们社会的精英力量有关。他们的存在表征着传统的继续,同时也在捍卫着一股永生的力量,可以让我们在迷惘之际洞见到未来的光影。有他们的存在,我们甚至可以相信我们民众的精神其实并没有贫瘠到极限。有鉴于此,我们的出版社冷落了这部分毫无商业价值的小众,实质上便是以冷落历史的近视举措轻松丢弃了未来。必须清楚,在这一点上,许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做法与我们很不一样。仍以美国为例,在这个处处依仗金钱说话的国家,非营利性质的出版社却也照样活跃,只是其规模大都较小罢了。它们和众多隶属大学的出版社一道,凭着编辑的良知及热情尽心尽力为公众奉献着有益精神健康的非消费性读物。结果表明,它们的多数出版物不是最畅销的,但却是最受读者好评的。在美国,这些非营利性质的出版社实际上是扮演了严肃读物作者们的赞助人的角色,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优良传统的延续。我们都知道,过去的西方一直就有富豪赞助艺术家或文学家从事创作的历史;我们最熟悉的例子莫过于梅克夫人之于柴科夫斯基了。设若没有这样的赞助人,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也很可能就已夭折。显而易见,这些赞助人对于人类交化财富的创造同样功不可没。
我们可以没有这样令人艳羡的传统,但不能没有相应的反省意识。也许我们的实情决定了我们无法完全效仿美国,但是适当作些利润上的让步,有意保护一下非畅销读物的作者和读者,这难道有什么太过艰难的吗?需要指出的是,出版社这种利润保护主义的作为,特别是对于那些刚刚起步的无名作者堪称令其绝望的打击。当然,今日中国经济的突飞猛进已然在这方面造就了难得的生机。在时下的高校,一本学术成果的出版可以获得从学校到国家多个部门的资助,且资助的力度可能一个赛过一个。成果出版之后,作者还会因此受到所在单位的额外物质奖励。还有,今天的学者大多也不再像过去那样囊中羞涩了,自费出版一本著作对其根本造不成伤筋动骨的后果。事实上,为评职称自费出书在当今的高校非常流行。这种实际在畅销书并不那么容易把握的情况下,正好可以解决出版社的资源紧张问题。
现在,尽管单本销量一直无法突破历史记录,我们的图书总量却在不断创造着历史新高。书店的数量多了,规模大了,究竟是不是因为读者也多了呢?我不敢确定;我所能够确定的仅仅是作者多了。这些数量庞大又鱼龙混杂的书籍其实根本不需要我们来操心它们的销路,要知道,它们首先不是书籍而是商品,所以为其掏腰包的人不一定就是要阅读它们的人,而一定是有能力买下它们的人。此种商品除去阅读还有很多别的消费性用途,比如可以作为空间装饰,比如可以作为礼物赠人。不是有报道说,时常有大款和企业老总定期或不定期地不加选择地采购些图书捐送给老少边穷地区的孩子们吗?就此说来,时下中国图书市场的惊人吞吐量又怎么能不归功于消费主义的呼风唤雨呢?
因为与利润无关,出版社索性便抛却了自己的尊严,没有了尊严,又何来的权威?在这个时代,出书已然没有任何权威可言了。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权威依然有效,我们的出版市场还会显现得如此的繁荣吗?但,谁又敢说这不是一种虚假的繁荣呢?建立在元尽消耗基础之上的经济繁荣又怎么可能是持久牢靠的呢?
【点击查看更多精彩内容】
相关新闻:
网络出版市场现状浅析
2010年出版市场八大话题看走势
开拓境外出版市场扩大中国文化影响
口消费指涉的是欲望,欲望是一个空间性概念,而消费本身则也只在当下方存意义。故此,作为时间性的历史和未来皆必然要被逐出消费艾化的地界。
今天,我们每家出版社的选题报告单上差不多都会有"出版方式"这样一栏,上面标明"公费"、"自费"以及"资助"的字样。一项出版选题是否能够被顺利通过,首先取决的不再是作品本身的品质,而是此种品质究竟具有怎样的市场号召力。至于作品将会产生怎样的社会影响,似乎不是出版者首先要考虑的事情。他们真正担心的是自己的投入最终能有多大比例的产出。同其他所有公私企业一样,成本和利润似乎也成了出版社生死存亡的要件。我之所以使用"似乎"一词,是因为出版社的处境和其他企业相比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即使它们正在步入"改制"的进程,却也并未就像其他公私企业那样被迫在市场的火山口上跳舞。今天,企业倒闭已是司空见惯的事实。但我们还从来没有听说中国出版社的倒闭。虽然国家相关法规已有向民间出版机构松动的迹象,但出版社的组建仍旧属于国家行为,中国出版社的特权身份依然没有被动摇。在这个前提下,它们已经开始将自己纳入与所有市场实体平起平坐的地位,着手鼎力打造全盘商业化的运作模式。
国家经济体制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急剧转型,固然使诸多人士和行业产生了明显的不适反应,但也有不少人士和行业做到了从容应对。如果说作者属于前者,那么出版方就该属于后者。于是,学术著作于商业文化时代必然遭遇的命运自然就显现出来了,此种状况在资本主义国家早已不算是什么新鲜经验。问题在中国之所以显得格外醒目,一方面是由于它的头一遭出现,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这些作者们的出版权利(public right)未能得到出版社出版权力(public power)的起码保护。我们当然不会苛责资本主义国家的出版商应该对此类作者提供保护,因为出版在它们那里已绝对是彻头彻尾的商业化行为,出版商的出版权力始终需要听命于市场的指挥棒。而在我们这里,出版社的权力至少在此时还是完全能够独立于商业号令的。可是,出于向市场经济体制表达认同的迫切需要,他们单方面就提前终结了同作者之间的历史默契。多年来,和我们的很多期刊一样,出版社也一直自觉担当着培养作者的神圣使命;有不少作家或学者就是从某一个出版社成长起来的,编辑们是良师,也是益友。但到了这一时刻,他们摇身一变,迅速将自己装扮成了商人。于是,编辑的含义就此发生了质的变革。衡量一个编辑的素质,不再是要看他知识修养的多与少,重点是要看他商业眼光的高与低。作者把书变成了铅字,获得了合法书号,他的可怜目的便算实现了。
上述所指还是中国出版社在商业文化尚未全面渗透整体社会时的一种现状,而随着市场因素无孔不入的染指,以及全球视觉文化一致性的绝对兴盛,中国出版社方才真正开始遭逢些许来自市场的压力。那么可以想象,对于它们来说,除了无所保留地拥抱市场,还可能坚持什么吗?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商业文化繁荣的速度,总是紧随着视觉文化的发展脚步的。从电视时代到网络时代,不变的是人类视觉欲望因此获得的一次又一次空前满足。视觉那喜新厌旧的本性理所当然地将文化的进步理解成了不断升级的消费,事实亦的确如此,没有消费也便没有商业。但是,当阅读本身也变成了一种消费行为时,情况又会怎样呢?
千万别被消费剌激生产从而带来的商业繁荣假象所惑,归根结底,消费就是消耗;其生产过程正是又一次不折不扣的消耗过程,与创造行为所具有的丰富动力实质完全南辍北辙。在每一次带有消费性质的行为当中,我们势必享受的太多,承担的太少;索取的过多,给予得过少。所以,我们发现,摆在面前的图书在装帧、印刷、排版、纸张等方面变得愈发精美,而在内容上却越来越趋于低俗化了。这就是消费性阅读的实情,图像挤压着文字,趣味占领着思想。在消费文化统领一切的时代,唯有这样的读物才可能会有畅销的实力。这没什么好奇怪的,不要忘记,青少年的阅读障碍应是在电视普及之后才呈现出的一个广泛社会现象。电视影像不单消弭着他们的专注能力,也阻碍着他们之于文字的亲近;而网络的出现则促使这一境况更加地恶化了。如此残缺的阅读能力又如何胜任得了既往那些需要动用一定抽象思维的严肃读物呢?于是,因为没有市场,就连过去那些广受欢迎的文学作品也遭遇了寒冬。
不过,大众阅读能力的退化还算不上出版社遇到的最严峻挑战,真正令其痛苦的是读者数量的急剧萎缩。过去,一部普通的长篇小说动辄即可有上百万的印量,而今,印量能够过万就可算作是畅销书了。此外,尽管在人口数量上中国居世界之首,可一旦按照比例换算下来,我们的读者却少得令人汗颜。即便在这有限的读者群当中,受"书非借不能读也"这一传统借口的影响,又有几人愿意负担购书的支出呢?必须指出,这绝非属于个人经济承受能力的问题,而只不过就是消费习惯的问题罢了。我也仅在这一点上能对中国出版社的现有处境抱以同情,确实,同许多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读者不仅是量的问题,质的问题也同样令人悲观。
比较一下便知道了:由于禁不住出版商的怂恿,莱文斯基将自己和克林顿总统在白宫上演的那场丑闻匆匆成书上市,看好了要共同狂赚一把;然而大大出乎其意料的是,该书居然遭遇了美国民众不约而同的坚决抵制,从而使他们的商业美梦在瞬间即被断送。这就是发生在美国的出版事实,它在一定程度上昭示了美国读者的素质。可以设想,假如此书当时得以在中国上市,它有可能也会遭致这样的冷遇吗?可是,在指责我们的读者的同时,我们仍然不能忽略我们的出版社所应承负的社会责任。毕竟,身处印刷时代广大读者的阅读口味是由出版社来塑造的。它们的倾向不仅仅影响着作者,也影响着读者。倘若出版社完全摒弃了培养读者群体的主动意识,那么它们便只能被后者牵着鼻子走,走到最后极有可能就是落得个被抛弃的结局。众所周知,我们的出版社先是紧跟着影视走,后来又是紧跟着网络走,事实证明,它们已经在消费时代读者任性步调的引领下不知不觉跟丢了自己。
过分看重畅销,我们的出版社正在经营的无疑是一项与自我社会地位不甚相称的活计,身份意识已被其自觉置之脑后。资本化运作方式决定了它们所要面对的压根不是什么读者,而是千人一面的消费者。把读者变成消费者,即把读者奉为了上帝。在这种意识的支配之下,出版社的教化功能可以说已经全然丧失,社会精神文明的宏伟事业也因此变得岌岌可危。消费主义原则主导的图书市场无时无刻不在纵容着读者的自恋意识,让读者以为他就是这一方天地里的中心;每一本书都是为他一个人量身定制,每一行字皆是为了让他备感快乐才有了存在的价值。因此,在每一本书的面前,他都不可能萌生丝毫谦逊的心态。对他而言,一本书就是一件小小的商品,它的到来只是以为他的生活提供日常便利为宗旨,其中并无什么神圣可寻。商品从不指导我们的生活,它仅仅听命于我们作为主人的指使。顺乎这样的情境,书籍固有的一切内涵差异统统被遮蔽了。精英/大众、高雅/通俗、严肃/调侃等既有鸿沟被一一填平,这看似民主平等的胜利表象蕴涵的不过就是商业的霸权实质,正如后现代主义表面上之于一切权威的反叛,所欲表达的不过就是针对消费权威的顺从;其指归说到底乃是对于历史的无情取缔。
今天,我们许多人极为反感对所谓纯文学的认同,其内心实际上就是在表达着对于历史的急切拒绝以及对于当下俗文学现状的无比满足。消费指涉的是欲望,欲望是一个空间性概念,而消费本身则也只在当下方有意义。故此,作为时间性的历史和未来皆必然要被逐出消费文化的地界。一件精美的商品既没有历史,也不需要未来,它属于且只属于当下。消费实践的空间动力学仇视一切可能生成历史价值的商品,当然那些只为收藏而存在的商品除外(有必要说明的是,在此收藏行为本身同样亦暗含着一个消费的过程,故而使得其对象与其他商品的消费本质并无冲突)。正是基于如此一种念头,权威的
《人民文学》杂志在去年终于放下纯文学的架子,向阵营之外的郭敬明伸出了橄榄枝。并不是编辑们意欲否认阵营界限的存在,而是郭敬明加入所带来的期刊销量激增,让他们暂时可以忘却这一界限的存在。把期刊视为商品,纯文学相对于俗文学的优势亦便自动失效了。
似乎没有什么好责怪的,既然消费主义话语不给历史以任何的发言权,那么我们的出版机构也就有理由不选择坚持了。非畅销读物只要没有来自权威层面的压力,它们便干脆一概将其挡在门外。但为此受到损害的不仅是非畅销读物作者的出版权利,还有非畅销读物读者的阅读权利。可是又不能不承认,这数量极其有限的一部分往往就跟我们社会的精英力量有关。他们的存在表征着传统的继续,同时也在捍卫着一股永生的力量,可以让我们在迷惘之际洞见到未来的光影。有他们的存在,我们甚至可以相信我们民众的精神其实并没有贫瘠到极限。有鉴于此,我们的出版社冷落了这部分毫无商业价值的小众,实质上便是以冷落历史的近视举措轻松丢弃了未来。必须清楚,在这一点上,许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做法与我们很不一样。仍以美国为例,在这个处处依仗金钱说话的国家,非营利性质的出版社却也照样活跃,只是其规模大都较小罢了。它们和众多隶属大学的出版社一道,凭着编辑的良知及热情尽心尽力为公众奉献着有益精神健康的非消费性读物。结果表明,它们的多数出版物不是最畅销的,但却是最受读者好评的。在美国,这些非营利性质的出版社实际上是扮演了严肃读物作者们的赞助人的角色,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优良传统的延续。我们都知道,过去的西方一直就有富豪赞助艺术家或文学家从事创作的历史;我们最熟悉的例子莫过于梅克夫人之于柴科夫斯基了。设若没有这样的赞助人,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也很可能就已夭折。显而易见,这些赞助人对于人类交化财富的创造同样功不可没。
我们可以没有这样令人艳羡的传统,但不能没有相应的反省意识。也许我们的实情决定了我们无法完全效仿美国,但是适当作些利润上的让步,有意保护一下非畅销读物的作者和读者,这难道有什么太过艰难的吗?需要指出的是,出版社这种利润保护主义的作为,特别是对于那些刚刚起步的无名作者堪称令其绝望的打击。当然,今日中国经济的突飞猛进已然在这方面造就了难得的生机。在时下的高校,一本学术成果的出版可以获得从学校到国家多个部门的资助,且资助的力度可能一个赛过一个。成果出版之后,作者还会因此受到所在单位的额外物质奖励。还有,今天的学者大多也不再像过去那样囊中羞涩了,自费出版一本著作对其根本造不成伤筋动骨的后果。事实上,为评职称自费出书在当今的高校非常流行。这种实际在畅销书并不那么容易把握的情况下,正好可以解决出版社的资源紧张问题。
现在,尽管单本销量一直无法突破历史记录,我们的图书总量却在不断创造着历史新高。书店的数量多了,规模大了,究竟是不是因为读者也多了呢?我不敢确定;我所能够确定的仅仅是作者多了。这些数量庞大又鱼龙混杂的书籍其实根本不需要我们来操心它们的销路,要知道,它们首先不是书籍而是商品,所以为其掏腰包的人不一定就是要阅读它们的人,而一定是有能力买下它们的人。此种商品除去阅读还有很多别的消费性用途,比如可以作为空间装饰,比如可以作为礼物赠人。不是有报道说,时常有大款和企业老总定期或不定期地不加选择地采购些图书捐送给老少边穷地区的孩子们吗?就此说来,时下中国图书市场的惊人吞吐量又怎么能不归功于消费主义的呼风唤雨呢?
因为与利润无关,出版社索性便抛却了自己的尊严,没有了尊严,又何来的权威?在这个时代,出书已然没有任何权威可言了。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权威依然有效,我们的出版市场还会显现得如此的繁荣吗?但,谁又敢说这不是一种虚假的繁荣呢?建立在元尽消耗基础之上的经济繁荣又怎么可能是持久牢靠的呢?
【点击查看更多精彩内容】
相关新闻:
网络出版市场现状浅析
2010年出版市场八大话题看走势
开拓境外出版市场扩大中国文化影响
- 关于我们|联系方式|诚聘英才|帮助中心|意见反馈|版权声明|媒体秀|渠道代理
- 沪ICP备18018458号-3法律支持:上海市富兰德林律师事务所
- Copyright © 2019上海印搜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电话:18816622098